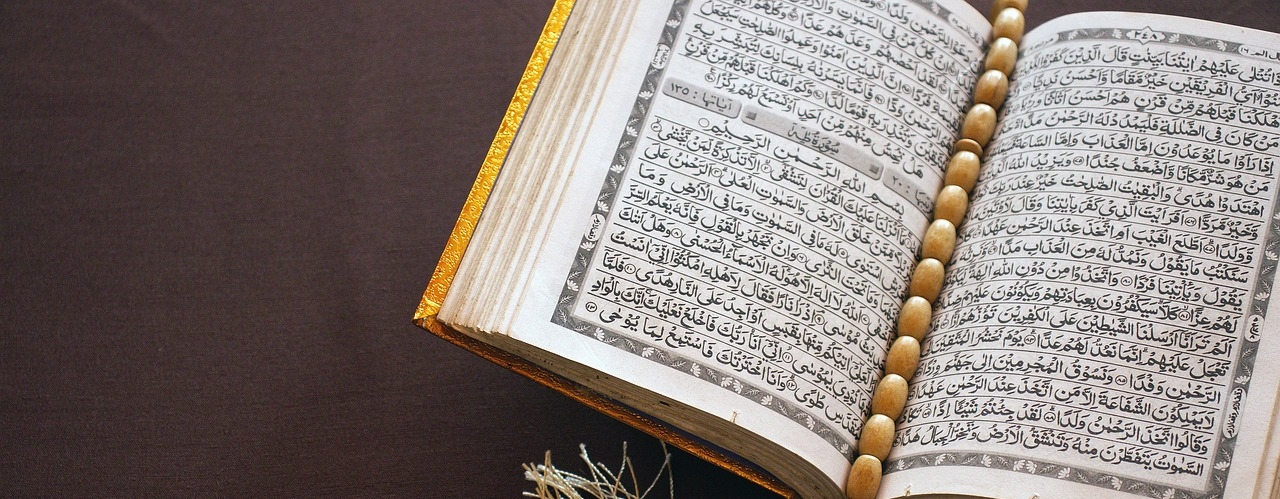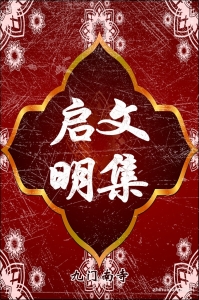
喧嚣和虔敬都已经渐行渐远,经历被时间隔成了段段短小的片段,除了记忆和体验在心灵里象流动的水一般外,我还能拥有些什么样的无法表述的历史呢?集体在我背后,孤单而沉重,我个人的叙述是否能够进入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的碎片中呢?坐在电脑前,思绪万千,我这个个人总是孤独的不得不常常和自我面对,直到清醒的意识到自我彻底的处于边缘。的确,这种边缘刻骨铭心。
春节到来的时候,满大街上摆满着各种各样的花和金黄的橘子树以及远离了根的桃枝。或贫或富的人们依然热情高涨的购买着那一些被视作“吉庆”的装饰,他们用那些充满象征的符号装点着家,于是家在那样一些简单的象征中忽然就有了意义。在这个普遍物化的时代里,我们要从那些经年累月的庸俗的社会活动中读出些“意义”并不容易。在节日里,人们拜年的拜年,贺岁的贺岁,祝福的祝福,自慰的自慰、、、、、、这一切构筑了整个都市短暂的春天。我们活在历史中,逃避不了甚至无法免俗。这不,有好些穆斯林的家里也摆设了几盆橘子树,树上挂满着金黄的橘子。金黄的橘子照样包含着象征,只是有些异样、、、、、、 我们都在异样的经历着盛大的异族的节日。
宰牲节来的时候,春节已然即将落幕,大街上已经弃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和金黄的橘子树以及远离了根的桃枝。似乎,当属于穆斯林的“意义”接近的时候,他们的“意义”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当我八点钟前往清真寺的街头时,我看到了一些勤劳的环卫工人满头大汗的收集清扫“象征”的垃圾。清真寺门口站满了比平时主麻多几倍的慕名而来的乞讨者,里面站满了比平时多几倍的前来礼尔德拜的穆斯林;警察在清真寺外严厉的维持着行人的秩序,阿訇在里面高声的宣讲着深奥的伊斯兰教义;寺里的宣礼塔下系了一头牛,门口的维族人的铺子前绑着几只羊、、、、、、这个时刻很庄严,我们这一群人感动的在清真寺里实践着它。而当我们走进清真寺后,外面的世界总是能够被我们骄傲的弃在街头,遥远的它们根本不可能触及我们的精神甚至肉体。这样的感觉令人陶醉,令人亢奋的想象着教门上的“牺牲”、“敬畏”、“纪念”、“忠孝”等概念。总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由衷的觉得满足,我们因为着我们的被慈悯而非常愉悦的感谢着安拉,并且暗暗思量着拜下来后要宰一个什么品种的多少斤两的多少钱左右的羊。伟大的安拉在《古兰经》上说:“动物的血和肉无法到达我,而你们的敬畏能够达到我。”我们就这样想象着敬畏,放弃了思想我们整个群体介于“民族和信仰”之间的模糊身份、、、、、、确实,历史的轨迹显示:在中国信仰伊斯兰的群体就是在那种自我心理满足的胜利中逐渐的滑入边缘的境地的,是在传统的意象符号认同中逐渐偏离教门的真实性的。而显然,这样的状况依然在持续着:在狭小的空间里以“边缘”的方式存在、、、、、、
当今天,我们无力应对生存的现实困境和文本的话语困境时,我们丧失的不仅仅是对“节日”的表述权,我们甚至丧失了我们自身。我们在拒绝同化的同时,我们所有的历史都在承受着被异化的身处边缘的苦痛。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切的思想吗?